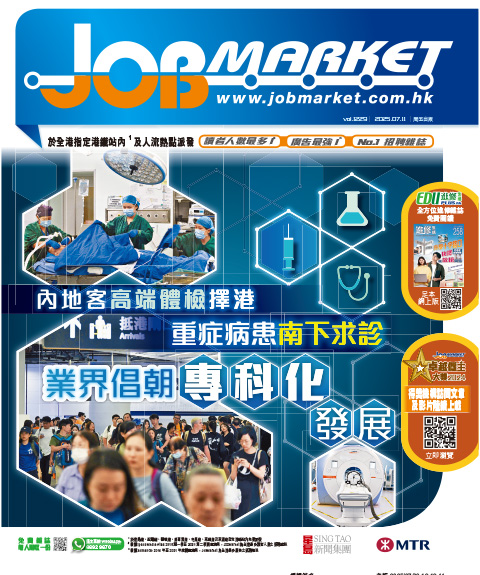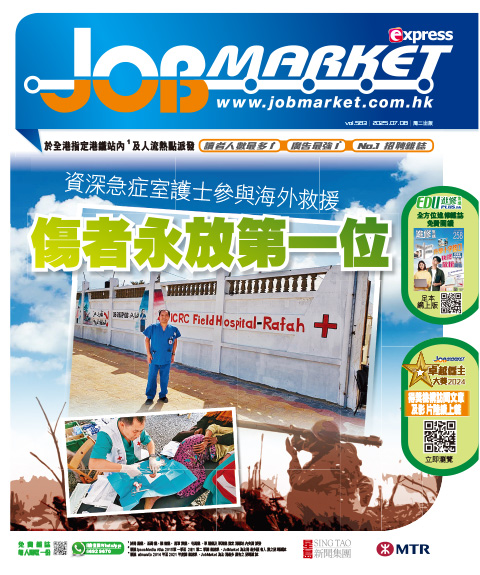港府近年大力發展鄉郊棕地,多塊土地被劃入北部都會區的鴻圖大計,繼而引發連串收地風波,當中不少散落棕地的廠房,正是極具香港製造特色的本土工業,反映棕地用途散亂。有被納入「元朗南發展區」的生鐵渠蓋廠,面臨逼遷但覓地未遂,四面楚歌;也有其他不屬於發展區範圍的廠房提心吊膽,擔心被趕盡殺絕;有豆品商未雨綢繆,多年前已買地保後路,但也有不少規模較小、財力較弱的小型鄉郊工業,坦言一旦收地等同結業,更對政府強調不會「一地換一地」、要廠商自生自滅的行為極為不滿。
近期多家本地傳統「老字號」廠房,因處於新發展區,面臨收地困境,包括志記鎅木廠、德保雪粒和悅和醬園。有鄰近志記鎅木廠的木工場尚未收到「最後通牒」,員工上下已人心惶惶,「老闆擔心!我哋做員工又驚無咗份工!」同區另一專營夾板、木枋訂製的公司,早於三年前遷出,「講咗十幾年有晒心理準備!知道拆就搬遠少少,應該可以捱多一兩年。」
源吉林茶歎難搬上工廈
不少鄉郊工廠擔心,政府會因發展計畫,在其他地區大規模收地,對碩果僅存的本地工廠趕盡殺絕。在西貢碧水新村自設工場,有逾百年歷史的源吉林茶,雖然尚未被納入發展範圍,卻早已思考相關問題。第七代傳人源樂明指,工場位於鄉郊,加上工友年事漸高,每次搬貨要行長長樓梯,數年前有意搬到工廈,「但每月數萬元租金,還有重置生產綫的成本,實在令人卻步。」
另覓場地重置的成本有多高?位於唐人新村的合豐鐵工廠,有近六十年歷史,生產及供應八成政府工程渠蓋,設有七萬呎廠房,因處於「元朗南發展區」範圍,是最早被收地的一批廠戶,一半土地自置可獲賠償。工廠原定今年8月遷出,最終獲延至明年第一季。第三代傳人陳滙璋不諱言,過去一年積極覓地,惟難以購買面積相若的土地重置,「前前後後找過二十三幅土地,由靠近邊境蓮塘口岸到流浮山附近的山旮旯都有!」
他指,其中五幅較符合當局要求,但問價時處處碰壁,「有幅地在北部都會區範圍內,業主知道土地或被收回竟臨時封盤,另有業主知道我們急於找地,由原本每呎七百五十元加價至一千一百元,令地價增至七千多萬元。」陳又稱,曾遇到村民反對,最終為免麻煩放棄上述土地。
渠蓋「噸噸聲」
廠房難遷廠廈
陳稱,最壞的打算,或會暫停香港廠房,改由內地直接運貨來港,但擔心中港交通受阻,無法準時供貨。他認為現狀甚為諷刺,「廠房由六十年代起見證香港發展,但現時亦因發展而隨時結業!」
外界有意見指,廠房應搬入工廠大廈,騰出土地作發展。陳坦言,並非外界想像簡單,提到一個渠蓋約半噸重(即五百公斤),平日約二十個為一組疊高放在空地,等同十噸重量,不宜搬遷至工廈,「一來搬運困難可能引致升降機失靈,二來擔心樓宇結構受影響。」
同在唐人新村設廠,有三十年歷史的何榮記鋼鐵工程有限公司,主要生產鐵欄、鐵扶手、鐵門及鋼門等,供應至公共屋邨。老闆何榮直言,至今仍未找到合適土地搬遷,「爛地一幅都加價至每呎租金二十元,以廠房佔地五千多呎,單是租金便過十萬元,還要興建上蓋存貨。」
賠償金「等足一年」
未找到地方搬遷之餘,部分廠商還未收到賠償。有同樣急於搬遷的小型工程公司慨歎,賠償金額「等足一年」,批評政府做法「離地」。
有未受波及的廠商形容,政府近年做法讓人「心寒」,並無思考本地廠背後的意義和價值,只向錢看,「你唔知佢幾時開刀,隨時下個到我哋!」為保產業,廠商各出奇謀,如壹品豆漿創辦人羅孟慶,其父早年曾經歷收地困擾,豆品廠由油塘搬至西貢,再遷往現址,由於香港地少人多,加上新界是發展重地,故五年前已在橫台山的工場附近購置土地作儲備,若被收地即可搬廠繼續經營。他說,慶幸當時找到一幅面積同是二萬呎,距離現時廠房二十分鐘車程的土地,終以數千萬元成交。
豆品廠買地自保
遷深圳成本增
有八十年歷史的樹記腐竹,原本在元朗設廠,第三代傳人孔穎儀指,早於八十年代因當局發展元朗,覓地搬遷困難,故放棄繼續在新界設廠,當時其父決定遷至深圳,每日將食物運港,避免「全軍覆沒」。她指,有相熟的豆品廠負責人透露,近年環保條例及污水排放法例日趨嚴謹,擔心一旦收地,除了覓地重置,新廠房更要符合嚴謹的法例要求,勢令成本大增。
現時沙田、上水等地設有不少「山寨式」豆品工場,當中不乏數十年老字號,但因廠房設施簡陋,只能供應豆漿及豆腐等予街市出售。其中一名東主稱,鑑於資本有限,根本無法擴充及成立現代化生產綫,令產品達致ISO(品質管理)標準,現時心態是「做得一日得一日」,坦言「收地之日,就是結業之時」。
早前,政府重申收地不會「一地換一地」,只承諾若廠戶找到私人土地,政府部門會簡化規劃及行政手續,並提供短期租約。對此,陳滙璋反駁,曾覓土地被指靠近綠化帶而不獲批,但他實地所見該綠化帶經已發展,但相關部門只按本子辦事,十分僵化。另一廠商亦稱,拒絕「一地換一地」根本是漠視地價昂貴的現實,存心讓廠戶自生自滅。